
附条件批准上市是指用于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疾病、公共卫生方面急需的药品,现有临床研究资料尚未满足常规上市注册的全部要求,但已有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疗效并能预测其临床价值,在规定申请人必须履行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基于替代终点、中间临床终点或早期临床试验数据而批准上市。
在附条件批准上市的技术要求中,对于治疗性药品而言,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对疾病的预后有明显改善作用;
用于对现有治疗手段不耐受或无疗效的患者,可取得明显疗效;
可以与现有治疗手段不能联用的其他关键药物或治疗方式有效地联用,并取得明显疗效;
疗效与现有治疗手段相当,但可通过避免现有疗法的严重不良反应,或明显降低有害的药物相互作用,显著改善患者的依从性;
可以用于应对新出现或预期会发生的公共卫生需求。
三代EGFR,附条件上市路径还走得通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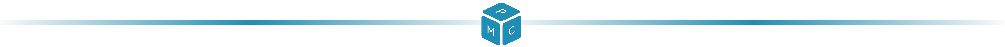
6月24日,吴一龙教授在某线上会议中再次提到:“最信服的证据只有来自随机对照”。
当然,附条件批准上市并没有要求必须是随机对照研究,特别是肿瘤领域,单臂和替代临床终点都是可以接受的监管考虑。而且,临床实践中的治疗药物选择也不是必须有头对头的研究才能决定,比如,在奥希替尼、阿美替尼、伏美替尼、贝福替尼、奥瑞替尼、瑞泽替尼和Limertinib全部批准上市的情况下,二线治疗如何抉择?
恐怕,也只能根据相关药物在临床试验中的表现,比如患者人群的差异、临床有效性数据和安全性等。当然,这7款三代EGFR抑制剂在研究数据上一定存在数值差异,但是否能够达到显著性呢?从数值上说,这几款药物的ORR普遍在60%~75%之间,似乎很显著。不过,ORR只是肿瘤在最短时间内缩小预定量(30%)的患者比例,并不能完全代表可以转化为PFS和OS获益,这时候也需要参考响应持续时间(DOR)。对于这几款药物而言,疾病响应深度普遍不足,在推荐剂量下很少显示完全缓解。
在临床获益的时间上,由于国内都是附条件批准,并没有确证的OS数据。而在PFS的评估上,基于Copy式的临床设计,让每个药物在患者基线上也有可比性,包括患者的中位年龄、体能状态甚至男女比例,特别是对治疗敏感的Del19突变患者比例,大多占比在61%~65%左右。mPFS的数值上,率先上市的阿美替尼为12.3个月,审批中的奥瑞替尼为12.6个月,是已披露数据中较长的mPFS获益药物。
其他的药物自然还可以从第4条即“疗效与现有治疗手段相当,但可通过避免现有疗法的严重不良反应,或明显降低有害的药物相互作用,显著改善患者的依从性”考虑。尽管,不良事件的发生数值有差异,但也有相似性(如具体不良事件),可以通过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严重事件(包括≥3级)以及最终的剂量中断、降低、停止和死亡等数据来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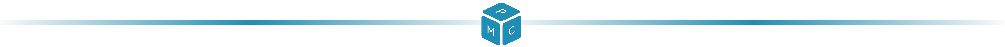
单纯就患者自付费用考虑,奥希替尼的负担反倒最低。当然,奥希替尼能够降价,原因自然也包括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的上市。但是,三代EGFR抑制剂却没有出现类似国产PD-1那般,远低于进口药品的价格。随着更多的三代EGFR抑制剂上市,三代EGFR竞争是否会演变为相似的PD-1格局?
另一方面,除药物价格考虑外,3家产品能否满足国内市场的治疗需求呢?这方面,似乎正在执行的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给出了参考。带量采购开启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同种药物具备3家通过(含原研和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上报的集采量是同期约80%的临床需求量。换句话说,3家企业已经具备供应80%的临床需求能力。
对此,吴一龙教授也在会议中指出,2~3家可能就能够满足,是否有必要上市10个药物?
总之,对于患者来说,上市再多的药物都没有直接免费更能提高临床的可及性。当然,基于患者的身体状况和不良事件具体情况,上市多个药物确实能够提供不同的选择,在这方面也是提高可及性的考虑。
对于监管机构来说,附条件批准的正确性和临床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在以患者为中心、临床价值为根本的初心下,三代EGFR抑制剂如何平衡临床可及性和确证性临床获益,也是备受挑战和关注的话题。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
 我是园区
我是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