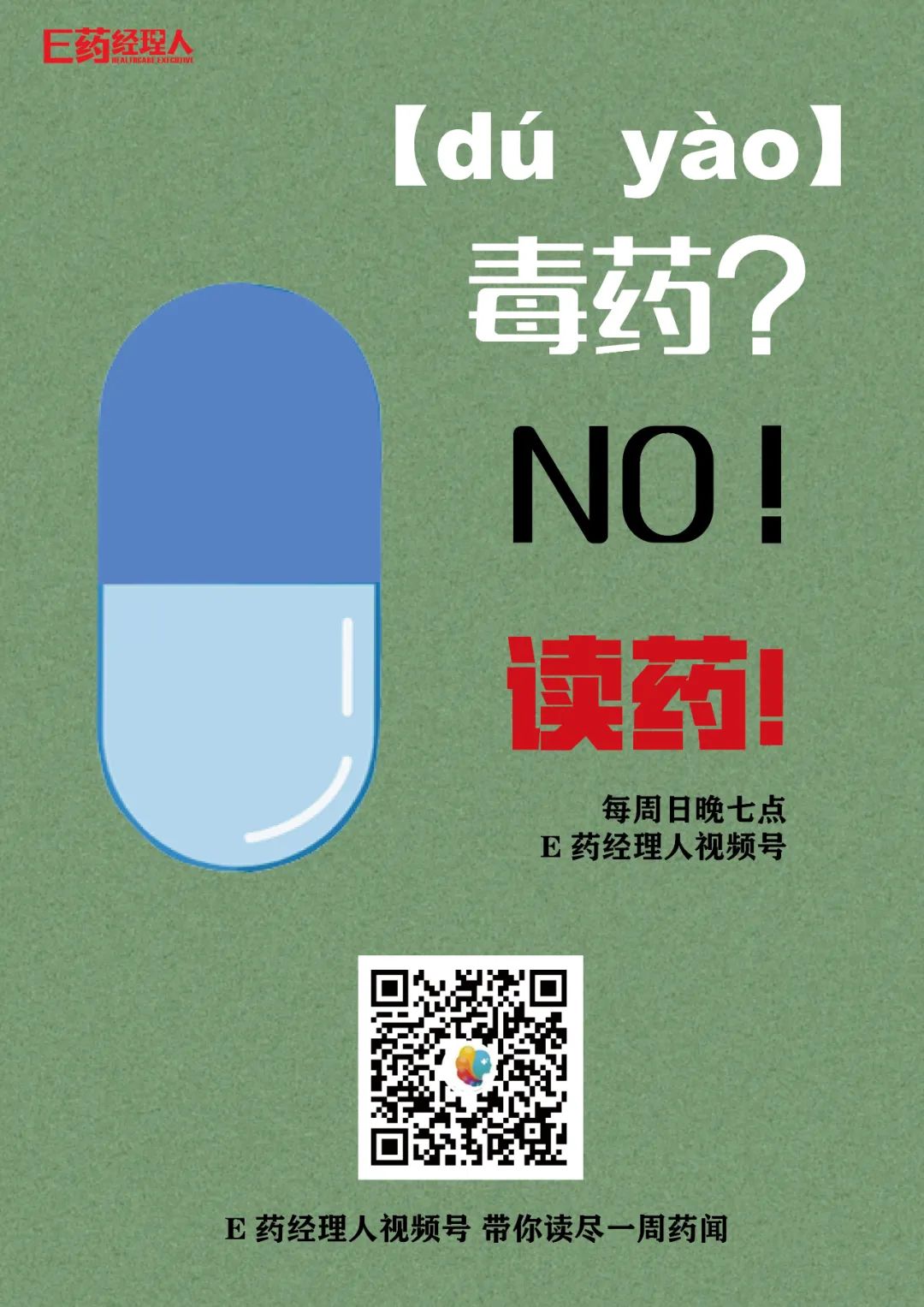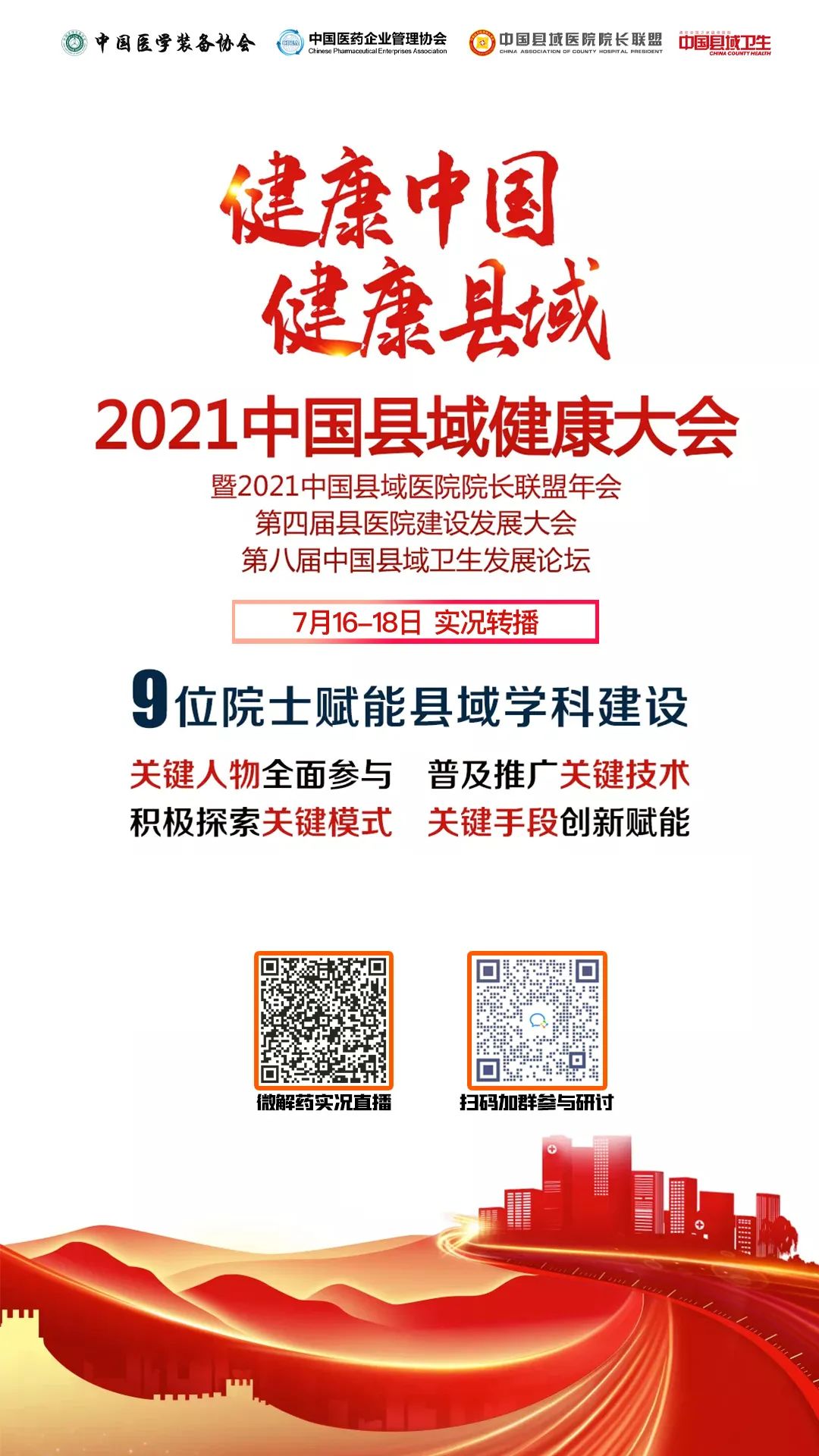院士集体把脉中国抗病毒研发,“解药”或系自然界,卡脖子技术仍需攻关,全球掀第三轮病毒药研发高潮
收藏
关键词:
研发
资讯来源:E药经理人 + 订阅账号
发布时间:
2021-07-17
新冠病毒流行至今已有一年多时间,跨过疫情的至暗时刻后,全球正重新点燃对疫苗与抗病毒新药的研发热情。
如今,虽然新冠疫苗的推出极大遏制了病毒的流行,但不断变异的病毒仍在向医药产业发起新的挑战。后疫情时代,人类如何与新冠共存?在抗病毒领域中,又有哪些赛道具备突出的发展潜力,能够推出革命性的药物替人类终结这一危机?顶级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2021年7月11日,由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支持指导,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主办,苏州市相城区望亭镇人民政府、苏州市相城区科学技术局、苏州市相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相城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E药经理人承办的2021(第二届)中国抗病毒药物研发大会在苏州举行。
来自国内的近200名抗病毒药物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投融资机构代表等聚集一堂,共谋抗病毒药物创新,探讨在中国可行的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在致辞中表示,一年来,医学界对病毒的研究突飞猛进,各类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成功,对于改造世界,控制病毒,保持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类做出重要贡献。未来,生物经济产业链的所有公司都应该紧密合作,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郜恒骏也指出,此次新冠让人类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的考验,并且至今仍在蔓延和反复发作。而去年12月我们国家的新冠灭活疫苗上市,为全球的抗疫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企学研融创新生态不断的建设,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行业将得到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
本次抗病毒大会上,多位院士和科学家阐述了疫情带给他们的思考,这种思考已经超越了狭义的病毒范畴,对医学认识论的发展也充满裨益。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就在会上提出,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一是整合,二是转向。
“为什么要整合?因为信息只有整合起来才能成为知识,知识升华了才能成为智慧,而智慧才是力量。”
面对突如其来的急性传染病和解决不了的慢性病,靠单个国家、单个专家、单个技术或药品的独自独斗是无法战胜的。只有构建起整合型的健康服务体系,包括科研、医学教育、医疗服务、医学预防和医学管理的整合,才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迎着风浪走,稳坐钓鱼台。
“但整合不是简单的相加,它是一门艺术。以会诊为例,要构建多学科的整合诊治团队,实现最大化的整合诊治效果。如今大家已都认可整合诊治将成为医学的方向。”

那么转向又是什么意思?樊代明进一步解释称,转向是指未来医学将从寻找病因转向修复人体的“自然力”。这种自然力有几方面的涵义:一是自主生成力,二是自相耦合力,三是自发修复力,四是自由代谢力,五是自控平衡力,六是自我保护力,七是精神统共力。
“当科学没有进入医学之前,我们是讲‘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但是现在我们找到了病因,认识了病毒、细菌,有了方向后,以此为靶点回来增强人体的自然力,这叫’改邪归正‘。我认为是抵御疾病最有效的方法。”
而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周德敏也认同,病毒既然来自于自然界,那么也一定能够用自然界赋予我们的武器来对抗它,关键在于发现这一武器。
周德敏指出,一个病毒的生命过程分为三个步骤:进入,复制,释放。相应的开发抗病毒药物也是在这三步上做文章,大部分的抗病毒药物都是阻止病毒复制,像达菲等药则是阻止病毒的释放。而目前以病毒进入为靶则构成了抗病毒药物研发新的契机。
他认为,本质上,病毒与宿主的相互识别过程是可被调控的,而如何开发小分子药物,来调控蛋白的相互作用,抑制病毒与宿主识别,改变宿主性,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研究中,周德敏意识到,细菌和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它就是自然界进化而来对宿主进行保护的东西,细菌有它的天然的来源,病毒肯定也有。HR1、HR2序列广泛存在于各种病毒膜蛋白里面,五环三萜是它作用的靶点,而五环三萜在自然界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植物里面有这么多的五环三萜可能就是用于自我保护的,我们应该从自然界里面找新的抗病毒的药物。
“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其中含有丰富且结构多样的酚类、多酚类、单宁类、萜烯类和生物碱等天然产物,均是长期生物进化核子燃选择的结果,基于传统中草药所含的天然产物的化学生物学研究,有可能成为发现原创生物产物的来源。”周德敏指出。
新冠疫情已经开始一年多的时间,中国也进入了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继续“健康中国”的行动计划,对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在本次抗病毒大会上,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就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他的洞见。
一是在没有病例的时候,主动地监视,提醒公众戴口罩、注意社交距离、减少聚会,通过打疫苗全力推进主动免疫。
二是一旦出现局部的聚集性疫情或散发病例时,要“五只手全部伸出去”。包括指挥系统的快速反应,核酸的快速检测,利用大数据快速地追踪密切接触者,加强医疗的救治和医疗设施的准备以及精准地强化对社区的管控。

他同时指出,因为体系设计上的原因,在这次抗疫中,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们防治结合的程度不够,即使在同一个体系内,上下不协同,各自为政的现象也使得单个医疗机构看起来虽然效率挺高,但整个医疗系统效率却不高。
梁万年认为,下一步的改革,应该是在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之间建立一套机制,让人员、信息和资源真正联动起来,进一步地整合体系。一方面,可以将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往上延,来满足更高层次的多样化需求。另一方面,也将这个体系往下延,聚焦患者出医院以后的医养结合,长期护理、临终关怀等延伸性医疗服务,使其能够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要整合体系,有两个局要破。一是组织机构的改革和再造,让优质资源真正从城市下沉到基层,也就是医联体和医共体的建设。二是保险方面的变革,在基本医保上,对待医联体应由传统的后付制变成预付制。在商保上也应大力发展,以满足多层次需求。“梁万年表示。
在这次抗病毒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以他对中国近一百年医药发展史的梳理为开始,向大家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医药发展是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仿到创,从无序竞争到有序的竞争,从多头管理走今天的科学管理的。
他同时指出,世界生物医药发展仍很艰巨,近几十年除了抗癌药和免疫调节药,其他领域尚没有很大突破。与此同时,我们的研发成本不断升高,回报率却在降低,很多药上市以后没有30年拿不回成本,所以中国的新药开发要注意平衡风险,也要意识到,如今的世界格局和疫情的形式,都可能会对医药产业创新格局的变化产生影响。
而具体到抗病毒这一领域,刘昌孝则表示,继艾滋病鸡尾酒药物和丙肝治愈药之后,生物医药在新冠的推动下,可能会迎来第三次抗病毒药物的高潮。应采用多种形式解决产业发展的技术问题,克服大而全,建立全新的产业研发系统。

刘昌孝认为,在细分的病毒领域中,艾滋病毒的糖基化位点是20到22个位点,而新冠病毒是65-70个,是艾滋的三倍。这意味着新冠可能随便换几个马甲我们就抓不到它了,这可能在诊断时造成漏点。“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科学的问题需要考虑,对于新冠疫苗的真实世界研究,必须能够表明它显著降低无症状感染、病毒载量及症状时间和程度。抗病毒新药从发现到开发也需要得到成药性证实。”刘昌孝表示。
在他看来,艾滋病也有极大难题需要攻克,一是天生有逆转录能力,能逃避免疫系统追杀;二是复制能力强,数量不断增加;三是高度变异性,很难有跟得上HIV变异速度的中和抗体对其进行攻击。
此外,艾滋病与宿主间还有个黑洞,HIV自然感染难以使宿主获得保护性免疫,这点又和乙肝不同。“目前不断有新的技术和模式出现,能够判断药物的有效、无效或者耐药,希望我们的科学家和产业研究专家,能够去验证它,可能会有收效。”
而对于乙肝病毒,刘昌孝认为,最难做的是cccDNA的清除问题,它目前还有很多科学和技术的难点。即使有一个靶点,可能不能变成现实,在临床上也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而对于改良性创新,像一些抗体、蛋白、肽类、小分子,它的连接体怎样带到靶上去,也需要探索试验来反复的验证。纳米药物也一直很热,但问世的产品基本没有。“不是我们不会做纳米,而是我们不会做纳米药,不会去评价纳米药。”
“未来,我们要更加关注创新驱动下的技术问题,自主自强地处理卡脖子技术。”刘昌孝指出。
最近一年,中国的新冠疫苗和抗体药物取得很多突破。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和肿瘤中心主任魏于全也就新冠肺炎重组蛋白的疫苗研究进展进行了分享。
在国家多技术路线疫苗研究的大背景下,魏于全团队选择了重组蛋白中的昆虫蛋白新冠疫苗的研发,目前已在进行三期临床。该疫苗是利用昆虫细胞在培养液中大量繁殖,将新冠病毒的基因引入昆虫细胞,然后将细胞作为工厂生产出高质量的重组蛋白,并进行纯化,该技术易于快速与大规模生产疫苗投入市场。
魏于全指出,未来人类与新冠共存可能是个长期状态,病毒在不断变异,为我们的疫苗设计提出挑战,它可能像流感一样每年都会来,所以即使从现在做新冠疫苗都不晚。“目前从国外的很多新闻来看,现有疫苗可以保护不发重症,但是不预防感染,这说明疫苗的研发还需要加强。我们也在致力于多价疫苗的研发,尽可能覆盖到多种突变。”
而具体到昆虫蛋白疫苗,魏于全介绍称,国内目前做这一疫苗的公司还比较少,昆虫细胞有很多优点,第一是细胞分裂很快,第二是生产的蛋白质量很好,安全性有保证。“赛诺菲用其做流感疫苗,有两三个产品已经上市了,GSK最早做宫颈癌疫苗也是用这个技术做成的。但国内还没有把它产业化,我们希望我们这次可以把整个的生产工艺建起来。”
在这次大会上,苏州大学药学院教授刘密也分享了他在新冠肺炎的疫苗和治疗性抗体上的研究。

刘密认为,在MRNA疫苗上,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稳定性,二是递送载体和递送技术的优化升级。而想要改善的话,在稳定性上,需要对它的序列进行进一步的修饰,另外就是从非编码区域进行着手改造。而在提高递送效率上,目前上市的效率最好的还是RNP,这个专利现在在美国手里。我们国家目前处在第二梯队,还要继续研发。
对于中和抗体的研发,刘密指出,传统的方式比较耗时,有些抗体还面临全人优化改造。而这两年的一个新技术是,通过分离康复患者血液中的单个B细胞,通过单个B细胞核抗原结合的细胞,来筛选潜在的有效的中和抗体,他们也正在来寻找和开发我们自己的中和抗体。
科学家们积极分享了自己在抗病毒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一个好的抗病毒药物研发该如何立项,进而找到自己在商业上的价值?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医药分析师东楠从二级市场的投资角度给出她的建议。

东楠认为,一个好产品应该用其科学性来说服资本市场。目前,在衡量一个产品或者药物的商业价值时,他们会更多考虑DCF模型。在这个模型里面,他们又会重点关注几个参数,包括产品的获批时间、发病率和人口的问题、年治疗费用、渗透率、净利润和获批概率等。
“在今年而言,二级市场对创新药公司有没有国际化能力给予了更多关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还是PD1单抗,目前四家国产PD1都实现了比较好的国际化。我们相信在抗病毒领域,未来也会有更多好产品产品能够走向全球市场,疫苗就是个好例子。”东楠说。
她还在在抗病毒药物的细分领域上,对几大病种的药物研发进行了预测。
东楠认为,未来几年随着国产替代的的不断完善,抗丙肝药物对于国产企业将有较大空间。而在乙肝领域,随着新药的上市和放量,未来也会迎来一个更快的增长。艾滋病用药的中国市场后续则会进入加速成长期,一些自费类的药物和一些新纳入医保药物的放量,可能会降低国家免费药物在市场中的占比。而在新冠的抗病毒领域,可能依然需要寻找一些特效药,来缓解全球疫情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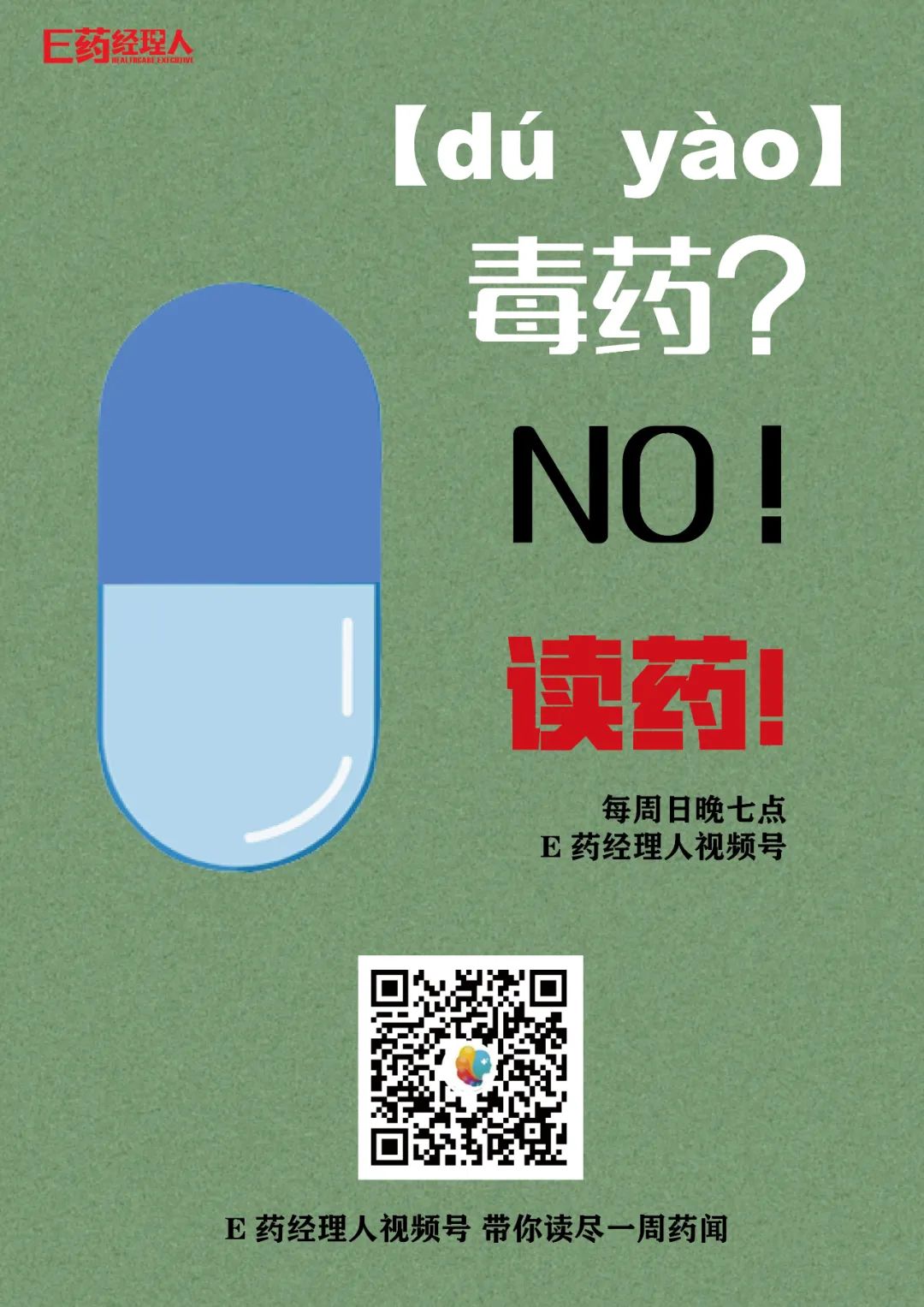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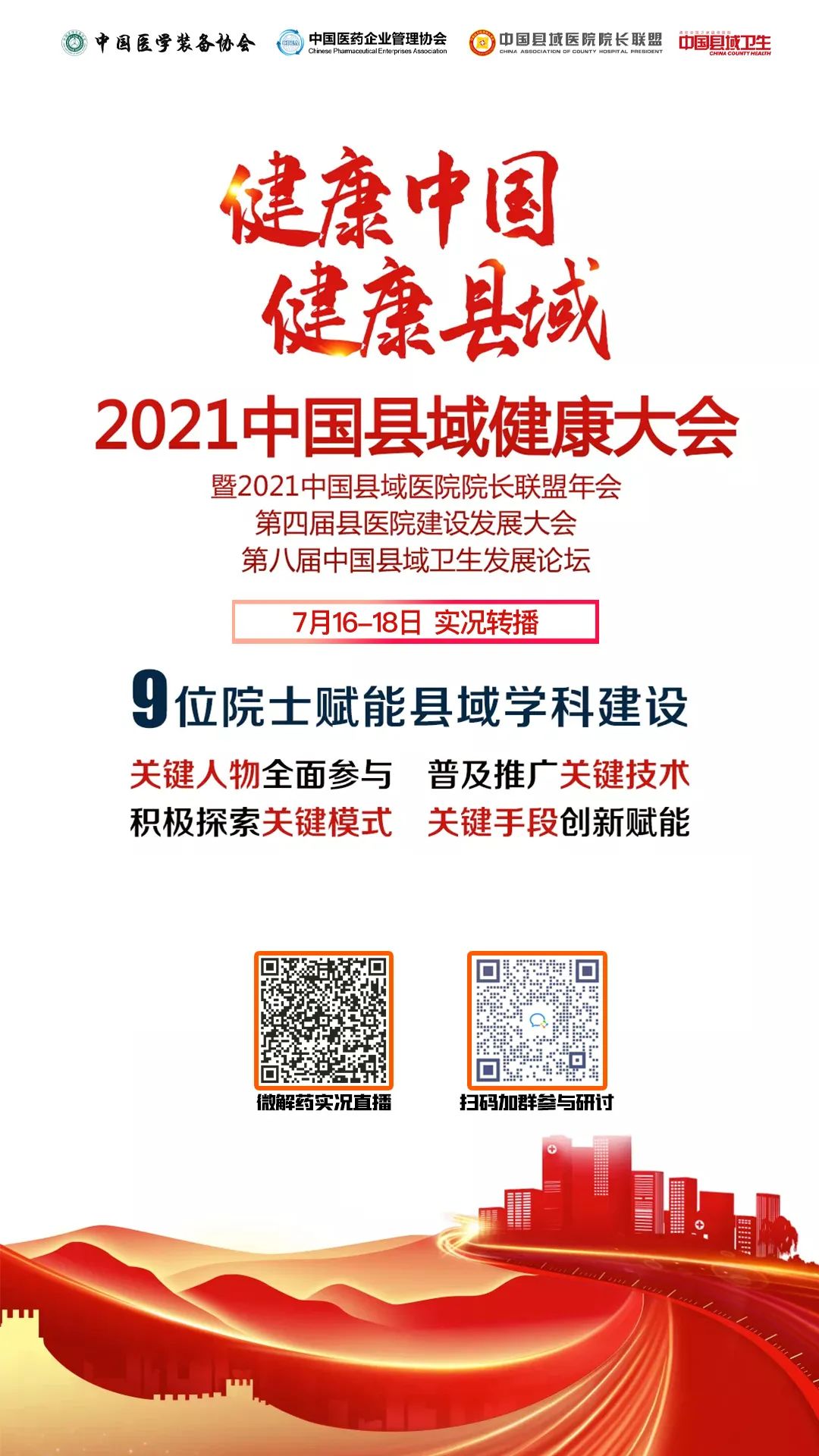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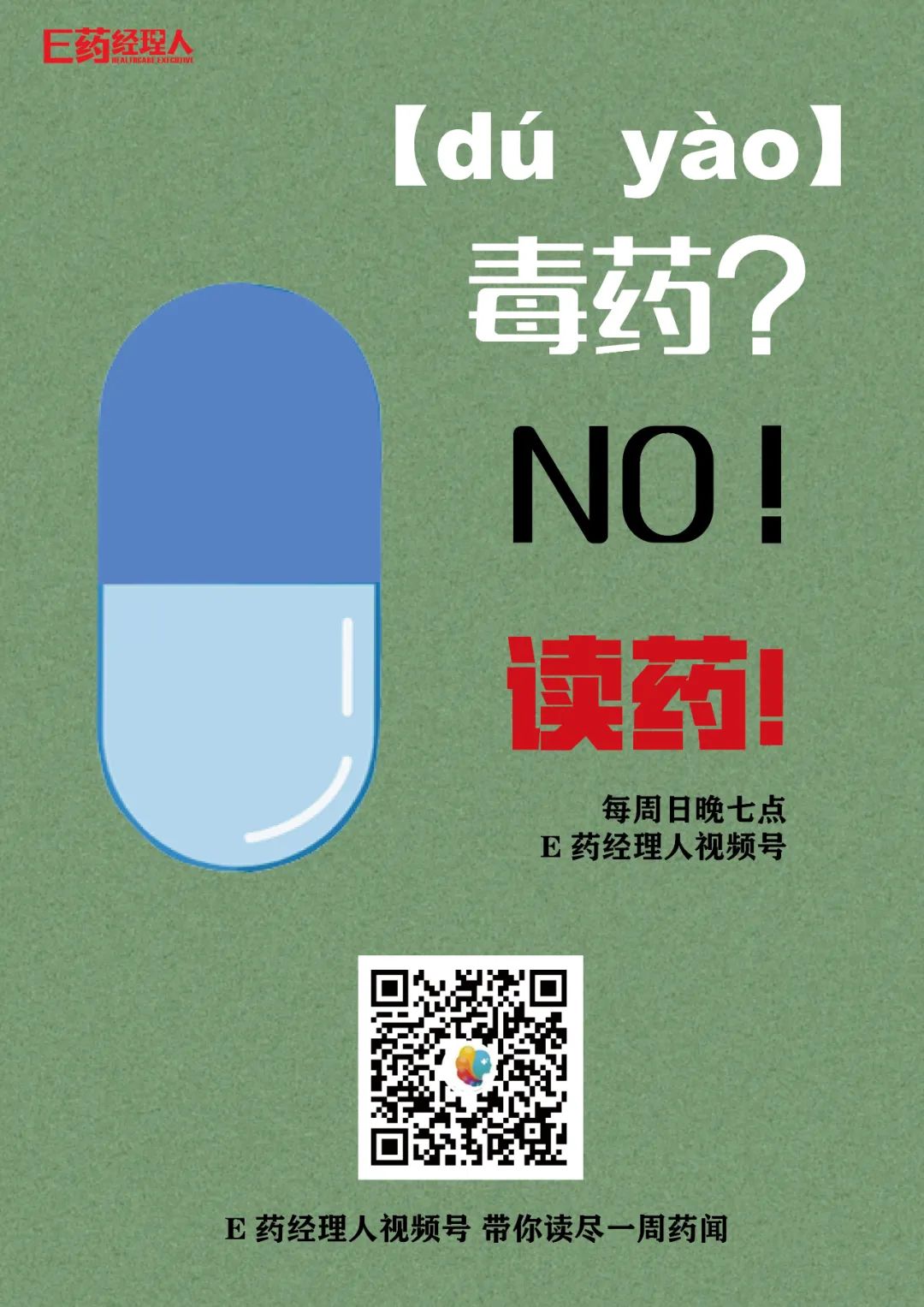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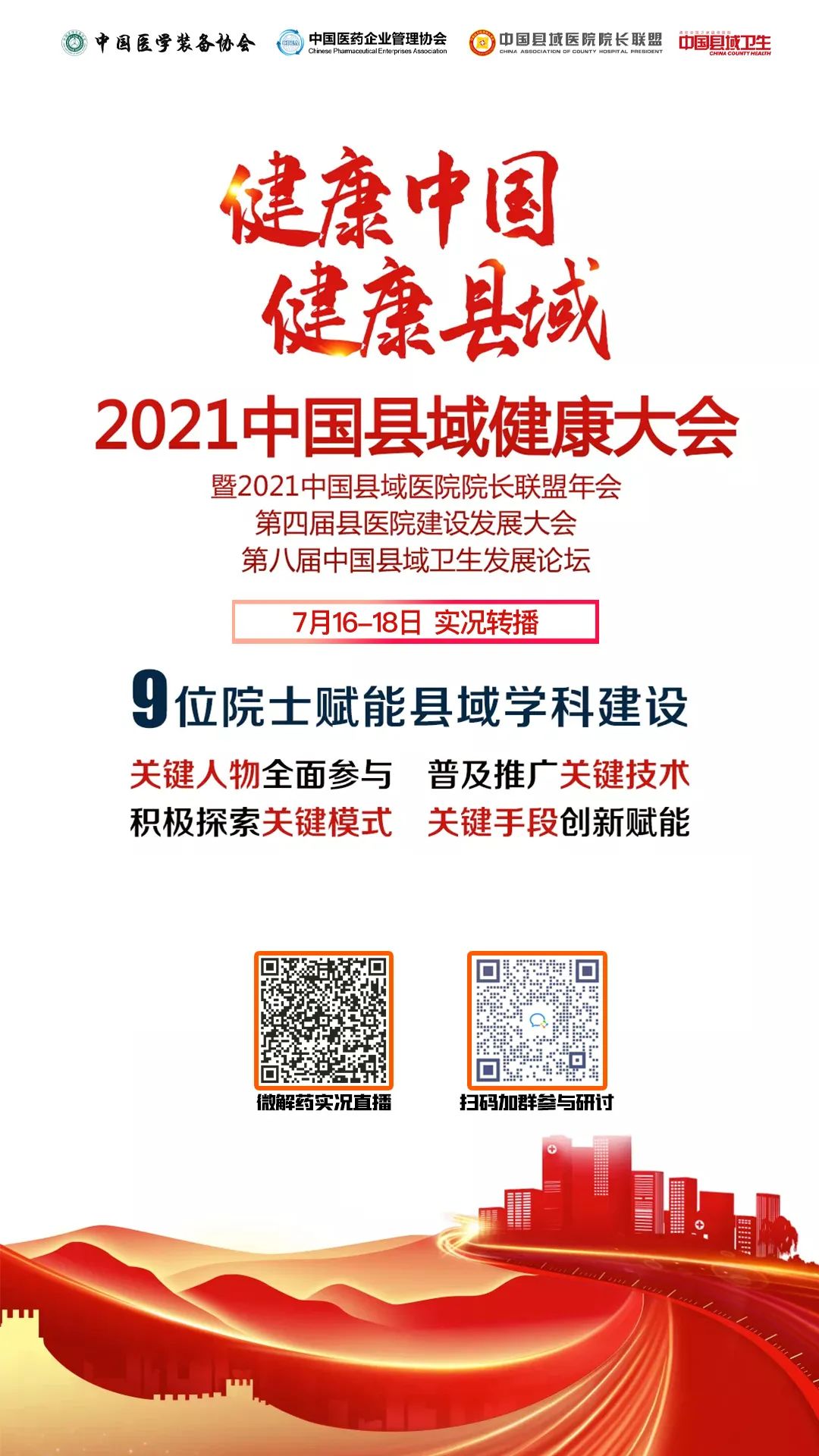
 药选址
药选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