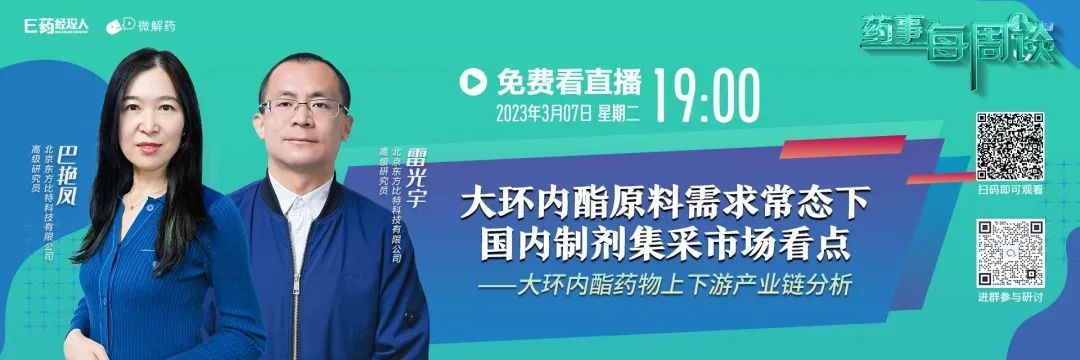多位与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医药工业十四五发展的主旋律,要通过产、学、研密切配合,以患者为中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才能使医药创新的科技成果实现产业转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直言,目前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能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提升,但目前创新大多还是以跟随式创新为主,从而造成靶点集中、赛道拥挤,进而引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也指出,中国缺少真正独立自主的,在全球有指导意义的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资本虽然对创新有加持,但资本不愿意冒险,谁也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所以真正的向国际市场看齐有意义的创新就很少。他认为这种创新需要国家来引导,而不是基金来引导。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医药产业的创新一定是开放式创新,不是由某个部门或某个群体来限定只支持某几个团队的创新。在民间依然存在着很多未被发现未被纳入国家体系支持范围的创新技术,这些民间创新有些甚至是在国际层面领先的创新技术。他认为,开放式创新模式目前还没有被真正的利用起来,需要大力推广揭榜挂帅的支持模式。
在医械创新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于清明表示,构建以领先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医等深度参与的高端医疗器械联合创新平台,加快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着力培育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观察到,目前国内医药产业从技术创新、研发、生产的环节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如何能够让这些具有原始创新的技术和产品进入医疗机构,实现医生和医疗机构无障碍地应用,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蛋白质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则强调了“科学家的素养”,他认为,在科学界,尤其是生命科学界,涉及大量基础研究的工作,但实际上有些并不具备转化潜力。有些科学家在较高级别的期刊发表文章后,就以为其具有转化潜力,“我认为这是不负责的一种说法”。科学家素养很重要,需要考虑这些科学经典是否具备医学转化潜力、是否拥有核心技术以及是否对得起投资人、政府、审查机构的共同信任。
在四川省政协委员、科伦药业总经理刘思川看来,中国创新药行业尚处于早期阶段,还没有出现在全球有重大创新影响力的公司,研发的产品还有很高的同质性,自研产品国际化路途不畅,企业兼并和收购才刚刚冒头。正是如此,现在正是孵育未来大型跨国制药企业的阶段。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生物制药CEO谢承润则建议,针对人类遗传资源临床试验审批可以试行“香港生物医药企业白名单”,不仅可以提升已落户港企的创新动力,而且能吸引更多的港资药企加快参与到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的大生态里。
此外,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药物研究院副院长闫凤英观察到,目前医保资金非常紧张,但是在医疗机构的医保费用覆盖中,有的既包括治疗,也包括一些类似于健康管理的项目。所以,建议医保资金要使用在真正的疾病救治上,而健康管理前期预防可以通过商业的途径去解决。希望相关部门在上述方面开展调研,在实际中把救治和健康管理界限划定区分清晰并妥善管理。
以下为“两会”代表、委员精彩观点总结(按照发言顺序整理):


于清明 全国人大代表、国药集团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医疗器械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关系到医疗质量安全与大健康数据的安全。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近十年来,在鼓励医疗器械创新政策的激励下,医疗器械创新生态发生显著变化,产学研医用各领域的创新积极性得到极大释放。创新医疗器械申请注册数量逐年增加。仅2022年,我国就批准了190多项创新医疗器械,其中国产ECMO、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等,很多是中国造、全球新的产品。新冠疫情使各国高度关注产业链安全。一些跨国企业正在转移和延伸产业链,医疗器械行业面临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短缺和涨价风险。
当前,各行各业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医疗器械作为大健康产业中的“国之重器”,亟须加快高端产品和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自主创新。对此,我主要提出以下建议:加大对高端医疗器械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骨干企业、行业组织协同发力,构建以领先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医等深度参与的高端医疗器械联合创新平台,加快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着力培育一批大型骨干龙头企业,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健康生活的新期待。

02.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在医药创新生态构建中发挥桥梁作用


郝海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创新能力也显著提升,但大多数企业仍以跟踪式创新为主,从而造成靶点集中、赛道拥挤,进而引发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尽管,近年来创新药企的研发项目,已经从之前跟踪跨国药企处于临床阶段的项目,前移至临床前阶段。但其本质还依然是以跟随为主,这充分暴露了我国在原始创新方面的不足,制药企业对于高风险、高投入源头创新项目投入的积极性不高,这种现状不利于我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的良性发展。
解决之道之一在于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与制药企业以及监管部门的协力与融合。高校、科研院所应当发挥基础创新的引导作用,通过校地、校企合作,培育更多原创成果,同时通过智库建设,在政府、药品监管、社会资本及制药企业间搭建良性沟通交流平台;通过整合多元创新要素,帮助和引导我国制药企业的研发布局能够真正聚焦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避免“跟风”式研发布局和同质化竞争。
另一方面,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能够针对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证、原创新药早期发现等,布局“重大科学计划”,引导和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原创药物发现阶段的深度合作;这样可以弥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对于暂时还看不到希望、不敢投入创新度高的项目的不足,这实质是制约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真空地带”。
此外,创新项目也需要制药界和临床医学实现桥接,进行联合攻关。但是要实现有组织的科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校和科研院所都缺少自身的资源杠杆,以调动科研工作者们的信心和兴趣,聚焦到需要攻关的领域。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其中发挥要素整合的作用。全国各地布局的生物医药园区建设应当进一步加强与高水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深度融合,避免过度量化和过度市场化的短期考核指标约束。
我国的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的优化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但只要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发挥政府的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进行创新要素和资源的整合,真正让“有组织的科研”落地生根,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生态跨越式发展为期不远。

03.多方面补足创新体系建设短板


朱同玉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医药创新体系建设尚存在几个短板需要补齐。
第一个短板是,目前国内的天使基金或种子基金的投入明显不足,与国际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现阶段的国内生物医药领域中,民间投资比例较前几年有明显的下降,尤其是天使基金投入不足,这是一个投资理念性的问题,比如对于投早期的顾虑。但实际上只有早期的投入,才会产生繁荣的后期成果。同时,政府在天使基金的投入上存在明显不足。不论是各地政府或国家层面的基金,早期投入偏少很多是受到母基金或国有基金考核指标的影响。目前大部分母基金与国有基金的考核指标往往需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但是对于天使轮投资基金而言,考核指标不应以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为主,而是投资项目所产生的创新团队、专利数量、培养人才数量、促进的就业等等,这也是国际上政府天使基金的普遍考核指标。
第二个短板是,创新的开放度不足,缺乏广泛的参与度。医药产业的创新一定是开放式创新,不是由某个部门或某个群体来限定只支持某几个团队的创新。在民间依然存在着很多未被发现未被纳入国家体系支持范围的创新技术,这些民间创新有些甚至是在国际层面领先的创新技术。我认为,开放式创新模式目前还没有被真正的利用起来,需要大力推广揭榜挂帅的支持模式。
第三个短板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当前我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进入制度化、常态化,涉嫌专利侵权(包括专利状态待定)的药品一旦纳入国家集采或在地方招采平台挂网,会直接影响专利权人的销售与利润,也会影响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升级。我建议,对于具有创新性的专利产品,延长其上市后的专利保护期,通过全链条的专利保护制度和行政司法协同机制,规范创新药和仿制药平衡发展、有序竞争,为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04.将政策驱动药企创新发展落到实处


生物制品需要创新驱动,而当前的现实是,中国医药产业的创新依然被诟病,不是对国外药物进行快速跟进,造成热门靶点扎堆,就是对海外产品授权引进,依赖国外的创新。中国缺少真正独立自主的,在全球有指导意义的创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资本虽然对创新有加持,但资本不愿意冒险,谁也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所以真正的向国际市场看齐有意义的创新就很少。我认为这种创新需要国家来引导,而不是基金来引导。
展望未来,建设健康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创新引导医药领域高质量的发展已成为共识。国家之前引导的重大专项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转型升级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生物医药行业要进一步发展创新,面对现实在创新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应该尽快组织出台相关的重大新药创新专项,正面引导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向高端,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立创新发展。同时,我也希望能和国内更多的同行企业一起,研发出更多先进的疫苗和生物药品。

05.建立创新可持续健康发展生态


王贵齐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

06.多方聚力,政策协同,孵育中国本土跨国药企




 谢承润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生物制药CEO
谢承润 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生物制药CEO

08.建议增设更多社会性心理精神疏导机构


我们的调研发现,随着现在生活节奏愈加紧张,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社会人群中存在心理问题的人群比例大幅上升,未来几年比例应该更高。
虽然现在医院里有一些精神心理问题相关诊室,在小学、中学、大学等都设置了心理咨询师,配有心理咨询教员,开展相关心理问题前期干预。但从实际调研中了解到,绝大部分真正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并不愿求助学校的老师和心理诊室,从疾病心理问题特点考虑,学生反而希望求助倾诉陌生人。
所以,我们呼吁建立更多社会性质的心理前期干预诊室或心理疏导室等。在前期没有发展到必须药物治疗时,从而进行一些专业的正规干预,减少往后期重症方面发展的比例。
此外,目前医保资金非常紧张,但是在医疗机构的医保费用覆盖中,有的既包括治疗,也包括一些类似于健康管理的项目。所以,我们建议医保资金要使用在真正的疾病救治上,而健康管理前期预防可以通过商业的途径去解决。希望相关部门在上述方面开展调研,在实际中把救治和健康管理界限划定区分清晰并妥善管理。

09.“科学家素养”需要重视


在科学界,尤其是生命科学界,涉及大量基础研究的工作,但实际上有些并不具备转化潜力。有些科学家在较高级别的期刊发表文章后,就以为其具有转化潜力,我认为这是不负责的一种说法。科学家素养很重要,需要考虑这些科学经典是否具备医学转化潜力、是否拥有核心技术以及是否对得起投资人、政府、审查机构的共同信任。
其次,是关于企业合作者的诚信,比如是否能遵循合同,以及如果项目成功后,企业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颠倒黑白、诬陷、恶意诉讼等,导致两败俱伤。
最后,我呼吁中国的药企一定要真诚团结,为14亿国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帮助别人亦是帮助自己。此外,有一点在技术研究上的现象需要提醒大家,近几年生命科学领域较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水平增长速度较快,但千万别一窝蜂冲过去,大可不必,中国市场有限,比如PD-(L)1有大约两百家药企进行临床试验,既浪费投资人的资金,自己又累又没获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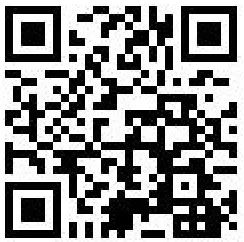
登记邮箱信息
订阅E药经理人
信息服务
扫描二维码

精彩推荐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
 我是园区
我是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