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职回国半年,33 岁的清华大学化学长聘副教授杨杰的最新成果终于发表,研究中他首次直接观察到了水分子的运动。
 图 | 杨杰(来源:受访者个人提供)
图 | 杨杰(来源:受访者个人提供)
2021 年 3 月,在海外读书、工作十多年的杨杰,辞去美国 SLAC 国家加速器实验室(下称“SLAC 实验室”)研究员职位,全职加盟清华大学。在此之前的 2019 年,曾在 SLAC 实验室和他“肩并肩作战”多年的李任恺教授也已加入清华。
杨杰是陕西西安人,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导师是祝世宁院士。直博就读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他告诉 DeepTech 此次研究拓展了关于水的新知识。
8 月 25 日,相关论文以《液态水中超快氢键强化的直接观察》(Direct observation of ultrafast hydrogen bond strengthening in liquid water)为题发表在 Nature 上,杨杰担任一作和共同通讯作者。
 图 | 相关论文(来源:Nature)
图 | 相关论文(来源:Nature)
液态水具备一系列奇异的宏观性质:它结冰时体积变大,导致冬天湖面自上而下结冰,保护了湖水中的各种水生生物。它的比热容异常之高,地球海洋极大地稳定了地表温度。另外,在人体内的各种代谢过程中,水作为天然溶剂存在,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微观层面理解液态水的性质,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
 图 | 大自然中的水(来源:Pixabay)
图 | 大自然中的水(来源:Pixabay)
液态水也是物理化学领域一个永恒的前沿,此前人们穷尽各种理论模型,也没能完全理解水的奇特宏观性质背后的微观机理。因为水不仅仅由单个水分子组成,分子间的氢键还组成了一个庞大网络,大量水分子通过这个网络共同决定着水的奇异宏观性质,其中的过程非常复杂。
让人“头疼”的水

此前所有的水观测都基于光谱观测,而杨杰采用了名为分子电影的新型实验方法,即给分子运动“拍电影”。由于电影需要在水分子运动的自然时间、空间的尺度下拍摄,因此不仅每一帧要能看清原子,每一帧之间还要足够快——需要达到飞秒级的速度——大约是眨眼时间的一百亿分之一。
过去的科学仪器中,“清楚”和“快”这两点很难同时实现。例如,电子显微镜是一种常见的、能看清分子结构的科学装置,但由于它的速度较慢,因此很难看清楚原子运动;飞秒激光光谱是一种常见的、能达到飞秒级速度的科学装置,但它往往只能借助光谱与理论模拟对分子运动进行推测。这就像是通过电话了解一个人。当你无法看到他,只能通过声音、讲话方式来了解他时,虽然可以对他有些初步了解,但效果往往没有当面面谈更好。
 图 | 实验概述(来源:Nature)
图 | 实验概述(来源:Nature)
理解水的另外一个障碍是理论中的“氢核量子效应”。氢原子核是最小、最轻的原子核,因此它的量子效应非常显著,这时就很难用经典理论去理解水分子的动态行为。因此,复杂的氢键网络、难以琢磨的氢核量子效应、间接的光谱实验测量,共同构成了液态水背后复杂微观机制让人“头疼”的原因。
通过结合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直接观察水原子运动

在该研究中,杨杰观测到了水分子内到水分子间的运动。通过把时间分辨率和空间分辨率两者结合,即可通过相关仪器同时实现飞秒级的时间分辨率、以及原子级的空间分辨率。
他告诉 DeepTech,即便从一个水分子运动到整个网络运动的第一步,之前也有各种争论。
有人认为必须穷尽一个分子内的拉伸、弯曲等等所有振动模式后,才能传到隔壁分子;有人认为由于氢原子质量较轻,所以要先穷尽各种氢原子的运动模式后,氧原子才会开始运动;还有人认为氢键可以直接和分子内振动发生耦合运动。但是,由于实验证据的缺乏,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很难说服对方。
 (来源:Nature)
(来源:Nature)
杨杰的观测和实验发现,分子内的氢原子运动可以直接导致隔壁分子的氧原子随之运动。而之前很多人所预言的氢原子的拉伸振动到弯曲振动,再到隔壁的水分子的振动这一系列运动耦合方式都没有出现。
到这里,之前人们认为的氧原子因为比较重因此可能是最后一个参与运动的观点直接被推翻。
 (来源:Nature)
(来源:Nature)
故此,杨杰的此次实验起到了一种为水分子超快运动“定标”的作用,通过该研究他直接确定了氧原子到底何时开始运动、如何开始运动、往哪里运动、以及运动距离等信息。
通过理论模拟,杨杰与团队还发现,氢核量子效应是解释氧原子早期运动的关键所在。杨杰的理论合作者分别采用了量子与经典方法模拟了液态水的超快运动,结果只有量子模拟可以重现实验结果,证明了氢核量子效应的关键角色。
这一实验明确了水分子内到水分子间能量传递的第一步过程是以人类可想象到的最快方式发生的,期间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因此,这一结果揭示了氢键网络中不同水分子之间的紧密联系。
将全球独一份的液体飞秒电子衍射技术带回国内

杨杰表示,该研究中发展出的实验方法,是一则通用性实验方法。样品并不局限于水,可以观测各种液体样品中的原子运动。
 (来源:Nature)
(来源:Nature)
事实上,该研究中使用的 “飞秒电子衍射”技术之前主要用于观测气体和固体。杨杰团队把它第一次应用到液体,因此打开了一扇观测各类液体中的化学反应的窗口。放眼全球,目前只有 SLAC 实验室拥有这类科学装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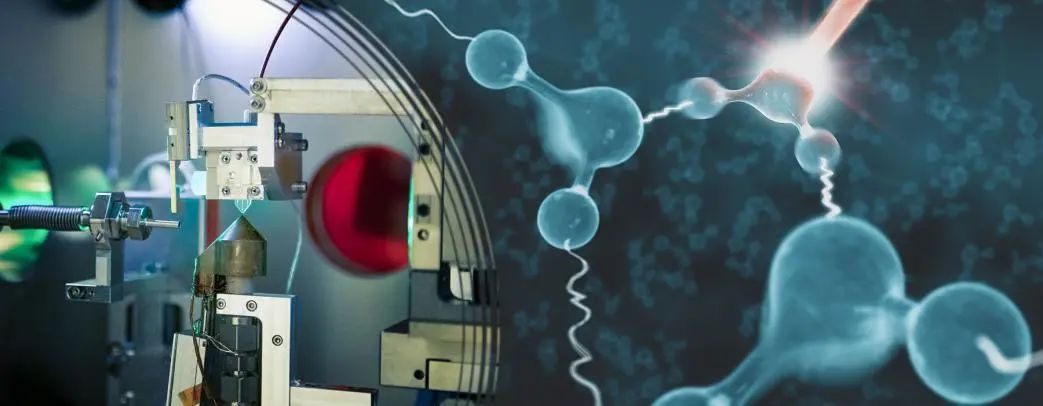
图 | 飞秒电子衍射装置(来源:Greg Stewart/SLAC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
这一装置具有相当高的技术门槛。不仅需要产生百万电子伏级别的高能量飞秒电子束,还需要产生真空环境下的纳米级液体薄膜。而液体薄膜需要具备自由流动、不结冰、耐得住电子束和激光的轰击等等一系列性质。因此,到目前为止,全球仍然只有 SLAC 实验室的一台装置可以开展这一类实验。
 (来源:Nature)
(来源:Nature)
回国最主要原因:清华提供的机会十分合适

杨杰表示,回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清华可以支持他心无旁骛地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他坦言这一实验技术的门槛比较高,需要依赖电子加速器、飞秒激光与真空液膜技术。想要做到世界前沿,扎实的技术积累、长期的仪器研发投入、紧密的跨学科合作、敏锐的科学直觉缺一不可。
 图 | 清华官网上的杨杰个人首页(来源:受访者)
图 | 清华官网上的杨杰个人首页(来源:受访者)
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需要物理、化学、加速器三学科交叉的基础研究。想要做到国际领先,研究单位既要有强大的工科支持,又要有全面的学科布局。由于清华拥有一支国际顶级的加速器团队与几十年的光阴极微波电子加速器技术积累,为这一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另外,学校非常重视基础研究的开展、交叉学科的建设以及特色实验装置的研发。因此,清华给了杨杰一个能够继续开展分子电影实验、专心攻克科学难题的机会。目前,杨杰的工作重点是在清华搭建一套 SLAC 的同类装置,并用它拍摄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液体分子电影。
关于这一技术的未来展望,杨杰认为,在化学领域,它提供了一种可以在原子层面“看清”化学反应过程的手段,为揭示许多反应过程与机理提供了一种强大工具。
 (来源:Nature)
(来源:Nature)
在生物学领域,蛋白质在发挥功效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动起来”,而冷冻电镜、X射线晶体衍射等技术可以看清蛋白质的原子结构,但看不清原子运动。这也是目前结构生物学的一大瓶颈所在。而分子电影技术有可能成为未来突破这一瓶颈的关键技术。
在年初刚来清华时,他在招募博后的朋友圈中写道:“我们课题组研究方向虽然比较小众,但科学意义非常重要,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长成为中国的‘分子好莱坞’。”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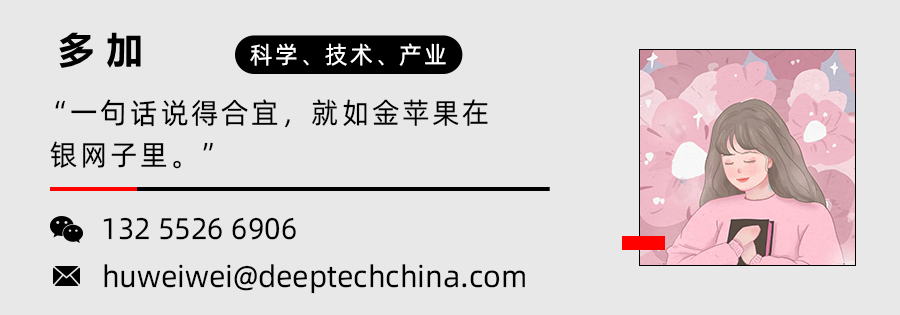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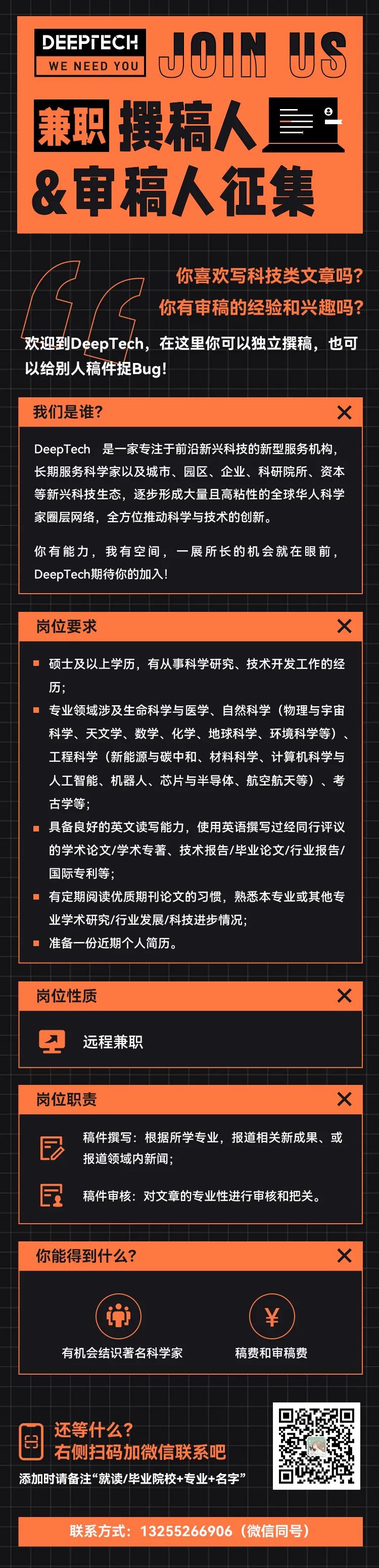



 个人中心
个人中心
 我是园区
我是园区





